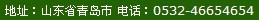|
治疗白癜风哪里好啊 https://jbk.familydoctor.com.cn/bjbdfyy_zx/ 在北京新工人剧场里, 举办着一场中国工人诗歌朗诵会。 乌鸟鸟站在台上, 朗诵着他写的诗歌《大雪压境狂想曲》, 天上的造雪工厂,机械的流水线天使,昼夜站在噪音和白炽灯光中,麻木地制造着美丽的雪花,超负荷的劳作,致使她们吐起了白沫。泄露的雪花,成吨成吨地飘落...... 乌鸟鸟是一个叉车司机, 失业之后, 他回到了广东老家,忙着成家, 前后相了三次亲,才和现在的老婆结婚。 为了扛起一头家, 乌鸟鸟背着行囊来到了广州。 人头攒动的人才市场,他显得有些拘谨, 但为了找到工作, 他试着给不同公司递上简历, 信心满满地给面试官念自己的诗。 然而现场没有人能听懂, 或者说没有人在意他念了什么, 他们在意的是能够赚钱的人。 格格不入的乌鸟鸟离开了人才市场, 繁华的城市灯火通明, 却没有他的容身之处, 如同他在诗中写的: “狼藉的古老丛林,淋着微凉的露水, 月光泛滥,远处传来了恐怖的人声。” 于是没有找到满意工作的他, 决定回家该做一个杀猪匠。 但他还是会拿起手中的笔, 写下对生活最后的反抗。 01 虽然没能留在大城市, 但乌鸟鸟算是幸运的, 至少他和爱人迎来了新生命。 而在煤矿工作的老井, 每天都要深入到地下米的矿井工作。 罐车缓缓下降,离入口越来越远, 直到地面最后一丝光亮消失, 对于他来说, 这与“下地狱”无差。 而这样的日子, 老井已经重复了二十多个年头。 张克良出生于年, 因为中考失利, 他早早就开始了工人生涯, 当过瓦工、搬过砖、挖过地基。 四处奔波的他, 为了一份有养老金的稳定工作, 就到了安徽淮南的煤矿工作, 开始了每天下井的生活, 之后便有了“老井”。上个世纪80年代, 全民都在看小说、读诗歌, 老井也不例外, 借此打发枯燥无味的生活。 一次,他在地下米的深处小坐时, 悄悄关掉了头顶那盏微亮的矿灯。 黑暗将他包围, 他悲哀地发现自己鲜活的身躯, 竟和四周死寂的物体一般暗淡无光。 从那时起,他便暗下决心, 要尽全力创造比肉身更明亮、高贵的东西。 而诗歌则成了他的信仰, 在黑暗的地心中闪着亮光。 我愿做一口活的棺材,一座移动的坟墓,殓载上你们所有残存的梦,一直往上走,一直走到地表,那个阳光暴涨的地方,再把它们释放出来。 年8月19日,淮南东方煤矿。 那里发生了一起瓦斯爆炸事故, 造成27人死亡, 他们被永远留在了矿井深处, 父老乡亲围在井口, 他们的焦灼表情刺痛了老井的心, 于是他写下了这首《矿难遗址》。 02 和老井一样, 陈年喜也在矿山打工。 作为一名爆破工, 他最擅长的就是打眼, 用铁管将火药送至深处, 留一根引线在外,随后点燃,往外跑。 这是最吃香但也最危险的工种, 整日与雷管、炸药、死神打交道。 因此陈年喜常常听闻工友受伤, 甚至去世的消息。 艰难的日子里, 陈年喜拿起笔开始写诗, 写下自己的生活。 年,一通电话打来, 陈年喜被告知母亲罹患食道癌, 此时他的父亲已瘫痪多年。 他没有任何办法, 只能继续在暗无天日的矿洞中, 埋下一个个雷管, 任由爆炸声敲击他的鼓膜, 然后写下一首又一首诗。 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,他们有病,身体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多少,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。——《炸裂志》 生活的幸与不幸总是交织一起, 出演纪录片《我的诗篇》后, 更多的人看见了陈年喜, 跟着剧组,他走上了电影节的红地毯, 甚至走出国门,站上纽约大学的演讲台。 但因为爆破工作,陈年喜的颈椎落下了病根, 年,他不得不做手术, 也不得不挥别他工作十六年的矿山。 而早在年, 他就确诊了右耳永久性失聪。 不仅如此, 年,“尘肺”还找到了他, 这不仅是生活带给他的“副产”, 更是他难以逃脱的宿命。 陈年喜说, “跟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很多人都死了, 只有他相对幸运, 只留下一只被炸聋的右耳, 还有一种近乎癌症的尘肺病。” 但在剩下的日子里, 他还是会走下去, 并且在沿途写下活着的质感。 03 邬霞,年出生, 14岁那年, 她跟着父母到深圳打工, 因为担心工厂不收童工, 她便借用了表姐的身份证, 过上了隐姓埋名的生活。 作为服装厂的女工, 她每天的工作便是熨烫衣服, 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, 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 身体上的疼痛尚且能忍受, 但精神上的痛苦, 却让她产生轻生的念头。 有一次,在被工厂管理人员训斥后, 她冲到公共洗澡间,推开窗户, 试图了结自己短暂的一生。 好在母亲一把拉住她, “好死不如赖活着。 只要活着,就一定有希望。” 单调乏味的流水线生活, 邬霞唯一的幸福, 是那些廉价的二十几块的吊带裙。 她会在深夜偷偷换上吊带裙, 悄悄溜进工厂女厕所, 当月光照在铁窗玻璃上, 她会对着“镜子”转圈, 独自享受片刻的浪漫。 包装车间灯火通明,我手握电熨斗,集聚我所有的手温。我要先把吊带熨平,挂在你肩上才不会勒疼你,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,多么可爱的腰身,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......陌生的姑娘,我爱你。——《吊带裙》 相比于其他人对苦难的描述, 邬霞的诗多了一丝调皮与乐观, 犹如石缝中漏进来的光。 就像她说的那样, “我一定会昂起我的脑袋, 向着阳光生长。” 04 王小波说过, 生活就是个缓慢受捶的过程。 不论是工人诗人, 还是平凡普通的我们, 即使心怀梦想,向往远方, 但总会被生活捶得措手不及。 于是乎,有人找到了发声的窗口, 它在纸上、笔下,在文字汇成的诗歌里。 就像某位作家写的, “诗歌,无疑是生活的一个出口, 一方面游走于生活的苦难, 一方面超脱的思想飞扬于自由的天空。” 阳光没有公平地照在所有人身上, 但谁不是一边喊着“人间不不值得”, 一边努力地活着。 “再低微的骨头里,也有江河。” 这是陈年喜给出的答案。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:http://www.hbkje.com/lcbx/3999062.html |
当前位置: 食道癌疾病_食道癌疾病 >当我们张嘴就是YYDS的时候,有一群人正
当我们张嘴就是YYDS的时候,有一群人正
时间:2023-1-12来源:本站原创作者:佚名
------分隔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上一篇文章: 永远的思念清明时节忆母亲
- 下一篇文章: 宝宝3岁前,父母谨记二不吃三不睡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