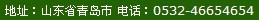|
苏孜阿甫片价格 https://m-mip.39.net/czk/mipso_4624735.html 文/王先生全文共约字 说实话,我和我的爷爷没有多少感情。这倒不是说爷爷对我不好或者我不懂得感恩,只是因为爷爷离开人世时,我才只有八岁。 别看当时我的年龄小,可那时的爷爷已经有八十一岁的高龄了。 01 那天中午,我斜挎着母亲给我缝制的布书包回家吃午饭,出乎意料的是,不是逢年过节的日子,大姑二姑三姑竟然凑拢在一起全来了,而且所有的人都围在爷爷躺着的那张铁架子床边。 所有人都沉默着,唯有母亲一个人在灰暗的厨屋里熬着梨粥。那天下午,爷爷闭着眼睛抿了两小口梨粥便彻底离开了这个世界。 整个西屋里哭作一团,大姑哭,二姑也哭,三姑胆子小,人也反应慢,可这阵仗让她也禁不住地往下落泪。 母亲在一旁扯我的衣角,“你也哭两声爷爷,他现在还能听得见。” 我记得很清楚,尽管自己被一团团哭声给包围着,可我就是哭不出来,我望着铁架子床上躺着的那个干瘦的老头儿,总觉得他像是睡熟了一般,也许第二天他就又可以在庭院里的墙根儿下披着大衣晒太阳了。 可是,爷爷终究还是没能醒过来。他被擦洗干净身子后套上了鲜艳的官袍,父亲轻轻一抱,爷爷整个身子就睡在黑色大漆的桐木棺材里了。 五天后,爷爷入土为安。伴随他一同消逝的,还有那个跟随了他一辈子的绰号——“大车”。 我曾经满怀好奇地问父亲,为什么爷爷会有这样一个绰号,父亲表示他也闹不明白,只是隐隐约约听说好像和爷爷早些年靠给人家拉大车为生有关。 02 爷爷年轻那会儿似乎是出过大力的,不然整个人也不会一直是精瘦精瘦的。可父亲却说,相比于老爷爷吃的苦,爷爷当年吃的那点儿苦根本算不上什么。 我的老爷爷,也就是我的爷爷的父亲曾经在天津小南门一带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。据父亲讲,老爷爷之前是给人家拉火轮的,因为头脑机灵手脚勤快,慢慢地成为了一个小头目。 后来因为和别人争地盘,脑子一热用铁锨把人家的身子给捅了个窟窿,这才不得不回到山东老家避风头。 这风头一躲就是大半辈子,在鲁西南的这块大地上,他有了自己的血脉。我的爷爷便是他的大儿子,至于他的小儿子(也就是我的二爷爷)因为贪水二十岁不到就被阎王爷给带走了。 爷爷年轻那会儿是怎么度过的,父亲说不上来,我自然也是没有什么头绪的。可有一点做不了假,那就是爷爷后来参了军,而且还参加过淮海战役。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每逢北风起,爷爷都会裹起他那件军大衣。爷爷穿军大衣有一个特点,那就是任凭北风吼得再欢,他就是不肯缩脖子。 “当兵的,再冷也不能缩脖子。”这是爷爷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 也就是因为那件军大衣,每逢年根儿,母亲都能从镇上领回一刀挂历、几斤蜜三刀,有时还能捎回几个印有“奖”字的白瓷杯子。 03 大概是曾经当过军人的缘故,爷爷的脾气总是显得有些急。父亲经常在饭桌上回忆起爷爷冲着小护士发火的那段往事,这就更加深了我对爷爷是个急性子的印象。 那一次,爷爷之所以会将一团火气撒在一个年轻的小护士身上,内中的缘由父亲再清楚不过了。那时,奶奶因医院住院治疗,可能是因为发烧导致血管变细了,那名小护士扎了好几次针愣是没能扎进静脉。 “吃不了这碗饭就赶紧走人,快叫你们护士长来!”这是爷爷在病房里吼出来的一句话。 尽管奶奶摆手要爷爷不要动怒,可看到手上被扎了好几个红色针眼的奶奶,爷爷就是控制不住自己,当年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怒气一下子就冒了出来。 脾气大归脾气大,可爷爷终究不是一个暴虐的人。在我的印象里,爷爷的脾气并没有那么大,有时候还让人感觉好相处得很。 也不知道怎么了,我现在一回想起爷爷,满脑子都是他在冬日的暖阳里抽烟袋的场景。爷爷是一个老烟枪,大半辈子烟枪不离手。就像其他会过日子的老头儿一样,他烟枪里的烟丝都是从集市上按斤称来的。 这些焦黄的烟丝极容易受潮,所以爷爷经常会蹲在旧报纸旁晾晒烟丝,有时候还会把一小撮烟丝在掌心里揉搓上半天,然后捧在鼻子底下猛吸两口,紧接着仰天长叹一声,好似充满了无限的满足感。 04 那年头儿家家户户日子穷,可再穷爷爷都不舍得在我身上省铜板。我至今都记得爷爷从上衣最里层的口袋里摸出一沓纸币,然后从中抽出来一张十元的塞到我掌心的情景。 那天我本想讨五角钱去买包白象的方便面,可谁承想爷爷竟然给了我十元。当我将方便面捏碎后往家走,心里想着要不要将剩余的零钱交还给爷爷时,刚一近爷爷的身,爷爷就朝天吐出一团烟气,“小儿,钱你留着,慢慢花,想吃啥零嘴儿就买啥。” 说实话,那天的方便面到底是什么个滋味,第二天我就忘记了;可我忘不了,当爷爷漫不经心地说出那句话时,我很想扑到他的怀里,可爷爷似乎并没有想要跟我亲热的意思,依旧是旁若无人地鼓动着腮帮子抽着烟袋。 爷爷在我们全家人面前是不苟言笑的。可是,在他的那群老伙计面前,他常常笑得是满脸褶子,有时候还夹杂着猛烈的咳嗽声。 小时候,我们家是爷爷和老伙计们的牌场。鲁西南一带,老人家不喜欢玩纸牌和麻将,大家热衷于玩骨牌。这种牌说是骨牌,其实并不是骨头做的,似乎是一种合成塑料,不仅质地轻盈,而且耐水耐摔,可以长年使用。 05 可我们家的骨牌却有些“与众不同”——本来三十二张骨牌是一般大的,可是不知怎么了,其中一张“斜四”的骨牌却被家里的猪给拱了,角落里残缺了好大一块。 也正是因为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,现在每次我和父亲母亲玩骨牌,父亲总是会提起那张曾经被爷爷“猪口夺食”救出来的骨牌。 爷爷当年用过的那副骨牌早就不知道被收到什么地方去了,可即使能够找到,我们再也不能回到那个湿漉漉的夏季了。 每逢夏季,鲁西南常常会接连下上好几天暴雨。暴雨送来了蛙鸣,也带来了爷爷的牌友。在堂屋正中的八仙桌上,四位“赌博鬼”两两相对而坐,秫秸杆一破为二,用烟头烫出几个黑点来,这就是色子了。 印象里,在潮湿的雨季,我们家堂屋里永远是雾沉沉的,这种雾不是外面飘进来的水雾,而是几位老爷子烟袋里蔓延开来的烟雾。 我喜欢在八仙桌子下面钻来钻去,可爷爷似乎并不喜欢我在旁边闹腾,“小孩子不能钻桌子,不然以后没出息。” 这是爷爷对我的恐吓,也是对于母亲的指令——这孩子该好好管教管教了。 06 小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很慢,总觉得身边的亲人会一直等着自己长大。可是,二零零一年,爷爷终究还是没能战胜癌症,在沉寂的午后不甘心地撇下全家子走了。 爷爷的确是得癌症走的。至于是哪种癌,父亲有时说是食道癌,有时又说是肺癌。可不管是哪一种癌症,爷爷生平的所作所为都为它埋着病根儿。 如果说爷爷得的是食道癌,那很有可能是源于他的急性子。 在部队当兵那会儿,吃饭是不能细嚼慢咽的,为什么?部队说驻扎就驻扎说拔营就拔营,如果饭点儿不抓紧时间吃,下一个饭点儿说不准就是两天之后了。 在这样的环境下,爷爷吃饭特别快,别人第一碗汤还没有喝下去几口,他手里的第二碗汤都已经开始见底了。 “喝汤要想不烫嘴,就得沿着碗边喝,边转边喝,边喝边吹气......”这是爷爷在部队里总结出来的快速吃饭法则。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进食热食的“巧方法”,让他的食道早早地落下了病根儿。 如果说爷爷得的是肺癌,明眼人都知道跟他的那把老烟枪脱不了干系。 不管是哪一种癌,爷爷在离世前确实是饱受了苦痛。当癌细胞开始扩散时,他的全身开始隐隐作痛。后来他觉得睡秫秸杆铺的床太硌身子,干脆就挪到了铁架子车的车兜子里。 与病魔默默抗争了大半年,那个不苟言笑的老头儿,肚子里填着小半碗梨粥便离开了这个他眷恋不舍的世界。 庄稼人不像城里人那样心细,爷爷没有交代他的后事。可父亲知道,奶奶的坟头早就起了几十年了,两个人肯定是要合葬在一起的。 07 现在回想起来,当年爷爷的葬礼办得并不风光。虽然父亲也觅了响器,可惜并没有找戏班子。整个葬礼上,除了此起彼伏的哭声和呜呜咽咽的响器声,没有一两句像样的戏腔。 幸好,爷爷一辈子不爱听戏。除了抽烟打牌,他最喜欢的东西就是肥肉片子和白蒸馍了。 去年回家,除夕的下午,父亲和我一同去给爷爷奶奶上林。父亲在坟头的东南角刨了一个窑儿,用筷子夹起一片肥肉平平整整地放了进去,然后再从最顶端的白蒸馍上掐下来一嘴馍。 “爹,娘,过年了,俺和俺小儿一起看恁来了。”父亲一边低声絮叨着,一边用打火机点起成沓的烧纸。“爹,娘,快来拾钱,该吃吃,该花花,别太节省......” 一套仪式下来,父亲掸了掸双膝上的灰尘,朝着灰暗的天空放了一只震天响的鞭炮。 鞭炮声唤醒地下的爷爷奶奶了吗?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——每年除夕下午的这场仪式,让每一位鲁西南人都可以与祖先有一次温暖平和的灵魂沟通。 那些已经作古的亲人,似乎并没有走远。不然,大年初一的供桌上也不会年年红烛闪动、香火缭绕了。 写到这里,我又想念我的爷爷了。爷爷,你现在还好吗? #农村老人# ——end—— 原创不易,期待您的
|
当前位置: 食道癌疾病_食道癌疾病 >一个山东农村孩子的独白想念我的爷爷
一个山东农村孩子的独白想念我的爷爷
时间:2023-4-10来源:本站原创作者:佚名
------分隔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上一篇文章: 经常吸烟的人,如果你没有这3个表现,恭喜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